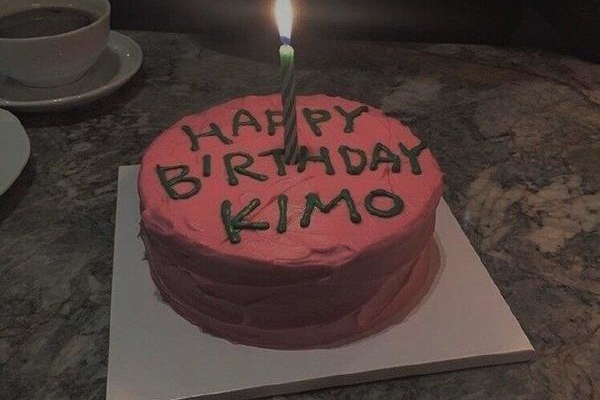1951年8月下旬,莫斯科阳光明媚,雅罗斯拉夫车站的汽笛声里走出一行中国留学生。
那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没有直航飞机,这群中国留学生在中苏专列上花了整整10天时间。370多名学生里有3个被分配到了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其中就有顾明远。
后来在克林姆林宫的新年晚会上,顾明远头缠白羊肚手巾和一帮同学们合影:两个姑娘一左一右挽着顾明远的胳膊,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小伙子双手交叠在腰间,和身边的苏联学生一比就显得有点拘谨。
顾明远是江苏人,但那年晚会上的陕北打扮倒是与他后来“憨直”的选择有些相映成趣:
在苏联留学5年之后,顾明远本来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但他果断放弃了苏联的研究生学历,选择回国。回国那年,顾明远27岁。
“当时就想着赶快回来报效祖国”,93岁的顾明远说起“报效祖国”腼腆的笑了。
后来顾明远成了新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科奠基人,不过真正令他释怀的却是另一件事:就是当年那个没在苏联念硕士的年轻人,后来却给中国数以万计的老师争来了文凭。
所以顾明远报效祖国的其中一种方式,是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有机会报效祖国——顾前路,明是非,意深远。
第一趟留苏专列
1948年,顾明远从江苏南菁中学毕业。不久后抗战胜利,青年学生都想要工业救国,班上的同学大多选择考理科、考工科,顾明远也跟着报考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不过最后他没能考上清华,为了维持生计,顾明远来到上海容海学校做了一年的小学老师。
解放初期的小学教育没有什么教育方法可言,但是初次做老师的这段时光让他体会到了培养孩子们成长的乐趣。“一年之后再想考理工科也很难了”,从最初的“不太想当老师”,到感觉“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顾明远想法的转变也只用了一年时间。于是转年的高考,顾明远顺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系。
1949年8月,顾明远从上海坐了53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平,他的学号是三八〇九四四。“三八”是入学的年份,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学号还沿用的民国纪年。
顾明远几乎天天泡在北师大的图书馆里。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他还读到了捷克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读完后激动不已,写了一篇读后感,被《中国青年》采用了。这大概算是顾明远的处女作,他拿到一笔不菲的稿酬,然后买了一双皮鞋。
在图书馆读到的这些文字中,或许就埋下了顾明远与苏联的不解羁绊。
1951年暑假的一个下午,顾明远和几个同学到什刹海游泳。正在兴头上,忽然有人叫他,说学校党总支书记找他谈话。书记问“如果派你到远方去较长时间,你有什么困难”。几天后,懵懵懂懂的顾明远去往燕京大学报到,参加留学考试。
这就是后来人们常提起的五十年代“留苏热”,而顾明远恰是新中国第一批公派苏联的留学生。
那时并不富裕的中国对出国学生的待遇却非常优厚,不仅所有费用全部由国家支付,书本之类学习用品统一发放,服装鞋帽统一制作,而且每人还配一大一小的皮箱。顾明远一行人在苏联的助学金由中国和苏联各自承担一半,每个月500卢布,是当时的最高规格。
来到苏联后,顾明远被分配到了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学院校长全然忘了这几位中国青年初来乍到语言不通,一路上滔滔不绝的介绍名胜古迹,顾明远对苏联人民的第一印象,就是热情。
“特别是抗美援朝取得了胜利,他们都把中国人当英雄看待”,顾明远清楚的记得在那段日子里也一直很受同学的照顾。
那时在学校旁边有一个文化俱乐部,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一有新电影,就给中国留学生最好的座位,购买电影票也可以免排长队。有一年,他们还组织留学生坐船从莫斯科经伏尔加河一路到黑海,走了来回二十天,游览了列宁故居、高尔基故居等名胜古迹,还参观了马马耶夫高地,那是曾经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得最为激烈的地方。
1956年夏天,顾明远本可以在苏联继续读研究生,但他回国心切:“那会儿算下来已经读了七年大学了(注:国内2年+苏联5年),所以没想当研究生,就想赶快回来工作。”
所有那个年代留学归来的青年都有一颗实干的心,那种忘我的想要迅速投身祖国建设的一腔热忱,一刻都不想耽搁。
只不过历史也在那个时间节点埋下了伏笔:急着要报效祖国的顾明远没有去读苏联的研究生,可是“教育学硕士”这张文凭有多重要,顾明远也是过了几十年才意识到。
“苏学中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一边倒”的向苏联学习的方针,比如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就是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手段之一。
顾明远在苏联的五年学习,主要聚焦在学生身上:“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和儿童文学,这些能更加了解孩子们身心的发育和成长规律。”
凯洛夫的《教育学》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中几乎人手一册,要求逐章逐节地进行学习。其中学科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的观点被奉为圭臬。这个理论体系影响了我国教育理论达半个世纪之久,尽管何为“教师中心”,怎样让教师堂堂正正的站在那个中心,顾明远也花了许多年才真正明白。
回国后的顾明远与夫人周蕖一起被分配到北师大任教。第一年,顾明远除了要上教育学公共课,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在西城师范建立实习基地:他担任教育学教研组组长和二年级一班班主任,带领教育系58届的学生在那里实习。
1958年,毛主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根据这个指示,当时的师大附中也开展了教育革命的工作。那年暑假,北师大派了约40名师生到附中搞“教育大革命”,附中校长邀请顾明远帮助他设计教改方案,“结果去了以后,他就把我留下来,不让我回来了,我在师大附中待了四年,当教导处副主任”。
那时师大附中只有一幢教学楼,是高中学生的教室和图书馆。初中学生都在平房的教室里上课。学校没有暖气,冬天每天早上顾明远都要生火取暖,但到晚上下班,炉子早已熄火,有时懒得再生火,就在冰冷的屋子里睡,“那时年轻,好像没有觉得什么”。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重视劳动教育,在中学广泛设立生产技术课,负责学生工作的顾明远时常带着学生在车间使用车床车一些小零件,每年冬天到附近农村收白菜,夏天去拔麦子,麦秆把手套都割烂了。
师大附中在琉璃厂附近,顾明远有时会逛逛旧书店,买几颗旧印章,其中有一块冻石印章,上面刻着“身行万里半天下”几个字,至今他还留着。
师大附中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所公立学校,有优秀的教育传统,钱学森就曾在这里学习了六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走出了一批在北京市很有名的教师,比如教高中代数的韩满庐被尊称为“韩代数”、教几何的曹振山被称为“曹几何”、教三角的申介人被称为“申三角”。
“在师大附中这四年,对我很有好处。因为过去我学的都是理论,虽然当过小学老师,但解放以前没有什么教育方法,在师大附中听课,我学到不少东西。我常去旁听一些课,听他们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后来顾明远提出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等一系列教育思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师大附中的“教育大革命”搞了九年一贯制、半工半读,结果教育质量下降,受到了北京市委批评,只好改回去,重新抓起教育质量。60年代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我国教育界也开始了对苏联教育模式的批判。
顾明远也意识到了全盘学习苏联教学经验的弊端。当时统一的教学大纲作为国家的文件,学校和教师无权更改。这种统一集中的领导,不仅抹杀了我国各地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性,而且使学校建设成为千人一面,办不出特色,学生的个性也得不到发展。他回忆起当时在苏联小学看到的课堂:“他们有比较形式主义的地方,比如很重视师道尊严,老师说的话就像‘圣经’似的,学生都老老实实地坐着。”
“我们的老师上课会让孩子们背着手,这个苏联倒没有,我觉得不应该背着手。”顾明远笑着提到,“我们和苏联在传统教育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像美国,他们的学生非常自由,上课的时候乱糟糟的。不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开始学美国的东西了,现在又提倡个性的发展了。”
1964年,教育系大部分师生到河北参加“四清”运动一年,顾明远因为体检发现肺炎,在北京休息,于是教育系便让他着手筹备刊物《外国教育动态》。这是顾明远做比较教育研究的起点。
“比较教育研究”几乎成了顾明远在中国教育史上最为人瞩目的标签,但回顾自己的教育生涯,顾明远最感欣慰的却是另外两件事。
教师不如售货员?
第一件事是从1986年开始,他花了12年时间主编的12卷《教育大辞典》,这部800万字的大辞典,是他和夫人周蕖一个一个字地看、一个一个字地改过的。顾明远说他们夫妇俩的研究方向有重合的部分,“她帮我很多,我们是互相影响”。
另一件事则是1996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通过决议,首次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对中国所有的中小学教师来说,这是他们真正站稳三尺讲台的一个里程碑,而顾明远铺设这条制度改革之路的起点,大约可以追溯到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
顾明远的《外国教育动态》曾在文革中停刊,与此同时,中国基础教育的教师队伍也在那段时间被严重破坏。
当时的情况是,教师队伍中的民办教师比例偏高,然而总体学历偏低,教师的受教育水平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80年代初,全国有842万的中小学教师,但是本科毕业的教师只有3%。
1980年,正筹备《教育学》教材编写工作的顾明远在武汉省委招待所有过一段故事,劳动人事部一位干部的饭后闲谈,扎到了顾明远的心里。
顾明远提到知识分子在当时不被重视,经济收入“体脑倒挂”的问题,就拿小学老师作为例子,结果对方反驳道:
“小学老师怎么能算知识分子呢?农村好多老师都是半文盲,村干部都对小学老师们说,你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去当合作社售货员!”
“教师不如售货员”的社会现实,在整个80年代都没有改观,顾明远也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医生有不可替代性,甚至连司机也不是谁都能当的,结果反倒谁都可以去中小学教书?表面上这是社会地位低、工资低的问题,但根源在于没有专业性,没有正规的学位进修,只能流于一般的短期培训。”
在顾明远看来,为中小学的教师建立学位制度,就如同工商管理的MBA,医学方面的临床医学一样,这一方面是门槛和凭证,但同时更关乎职业尊严。
1989年,顾明远在《瞭望》杂志撰文《必须使教师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篇文章对于后来在90年代开启的教师学历制度改革,有着开路先锋和划时代的意味。文中这样写道:
“任何一项职业,越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的职业性,它的社会地位才越高。可以认为,一项人人都可以干的职业,是不会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重的。……因此,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尽快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使得教师的职业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尽快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
彼时的顾明远正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1993年,他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实验中学、二附中和北京十一学校办起了研究生课程班,培养骨干教师。
自那之后,全国许多师范大学也都办起了研究生课程班,这也为1996年教育硕士学位制度的最终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年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首先开设了教育硕士学位班。
从教育硕士学位(MEA)确立之后短短数年的发展数字看,顾明远的这次推动是大势所趋:1997年,因为计划内招生名额的限制,总共录取了177人,一年后改为计划外招生,结果猛增至1400人,等到2002年,全国共招收8000人,并有29所师范大学设立的这一专业。
1998年,顾明远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一文,向广大中小学教师介绍MEA。一时间,向顾明远表达感谢之情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入了他的办公室。那些当年读了教育学硕士的学生在信里说,顾老师的这篇文章,他们都是复印下来珍藏的。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建立20多年来,已经有32万余人攻读,20余万名中小学教师获得了硕士学位。可是少有人意识到,为老师们争取到硕士学位的这位奠基人,66年前在苏联放弃学位的时候几乎不假思索。
尾声
顾明远今年93岁,从1992年开始,他在北师大英东教育楼七层的办公室工作了30年,他指着整整一面墙的书架,“书都放不下了”。
顾老如今说话的嗓音有些沙哑,耳有点背,时而听不太清周围人讲话,不过说起关于教育的往事,老人家的思路始终很清晰。
顾明远在今年春节期间有整整12天没有下楼,写出了一本十万字的《中国教育路在何方》。他觉得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把人忽略了,应该让学生真正全面发展,能够有时间锻炼身体,参加社会活动,培养自己的积极情绪,能够走向大自然,能够欣赏艺术,能够喜欢自己做的事。
顾明远也从未落后于教育的前沿问题。从1991年开始,他就任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技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技术的问题,我是外行,但是我可以从教育的角度谈谈我的观点”。比如最近流行的智慧教育,他就认为技术手段是为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让人更聪明,但是要处理好技术和人文、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有了人工智能是不是就不要学校、不要老师了,恐怕是不行的”。
顾明远说自己这些年因为糖尿病瘦了十几斤,每当有人问起他的长寿秘诀,他只是说自己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
“我不吃营养品也不看养生堂,我不听这一套,就是想着把学问做一做,没有什么别的要求,生活很简单。”
回看当年在克里姆林宫与同学的合影,顾明远缠着的白色头巾如今已成满头白发。顾明远的白发几乎不掺一丝杂色,似是对他数十年忘我与纯粹的见证。
【相关文章】
★ 为啥说过了这个年龄,就别再支持孩子考研了?背后原因,父母要懂
本文地址:https://www.qubaike.com/hotnews/81me5i0n.html
声明:本文信息为网友自行发布旨在分享与大家阅读学习,文中的观点和立场与本站无关,如对文中内容有异议请联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