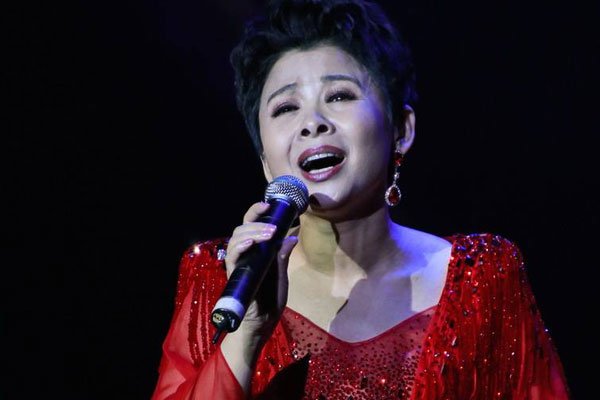在拉康对实在域的论述中,“断裂”一词出现频率极高,而“断裂”恰恰也是拉康对主体实在结构的最好隐喻。
正是原始场景本身的断裂,使得主体从“创伤”出发。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并且这种精神性创伤会将会无限反复在主体的梦中。
《情书》中,各角色主体在重复性创伤事件中与实在域相连,在被语言世界切割的剩余现实中感知死亡与缺失,试图在现实的裂痕中摸寻主体的存在。

死亡线索与缺席出现
当现实的完整在主体面前发生断裂,便预示着主体的形成过程将因此发生改变。实在是一个前象征的位置,这种实在需要经人类个体来体验,当它作为一种符号进入生活的辞说中时,此时原本的发源位置便以需要性的形式闯入现实。
影片中众多的死亡与缺席线索,都暗示实在断裂发生的源头,这一切线索都在象征着现实的缺失与空无。
“逝去的人总是会被遗忘的。”

这是藤井树(女)的母亲在谈论起她去世父亲时说的话。丧礼作为一种让死者尽快离开人间的仪式,符号秩序催促“死者”接受它的命令,回归虚无。
它让众人接受一个人死亡的命运,并尽可能地遗忘死者绝大多数的事情。此时的哀悼仅作为一个能指,其内容却是空的,并不指向任何东西。
在藤井树(男)三周年葬礼现场,故事展现出了人们对于逝者的不同态度:藤井树父母表现出对追悼仪式的厌倦,父亲被迫应付,母亲则装病坐在博子的车上准备回家;藤井树(男)的朋友们借追思会开了一个玩笑;生前一起登山的朋友尾熊留在他遇难的山峰上照顾前来的登山者。

这看似漫不经心的行为,具有将丧礼作为“遗忘机器”的功效,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对抗遗忘的结果。
而在两位女主角身上,她们的表现截然相反。面对缺席,一个沉湎于过往,一个逃避过往。博子抵御这种遗忘,试图将消失的空无延续至现实当中,依然处在藤井树(男)去世的阴影里,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藤井树(女)对于父亲的死亡一直表现出回避态度,初中时面对少年树的爱意也始终视而不见。影片中,角色在实在界的原始认知表现在,博子因藤井树(男)的离去产生了不完整的自我意识,试图对抗遗忘,否定现实。

当博子在翻开藤井树(男)的毕业纪念册的时候,这一过程已经开始,而纪念册上的地址,指向藤井树(男)的故乡——小樽。
于是博子寄去信件,这一行为我们可以阐释为博子抗拒藤井树(男)已死事实的惯性,但信件传达的必然失败又成为博子接受死者死亡的媒介。
信件奇迹般地得到了回复,对博子来说这是来自天堂的奇迹,但这一奇迹毫无疑问是空无的。
到达小樽后,博子面临着自我身份的缺席,使其一直处在“我”是谁的困惑中,这一缺失加剧了其自我意识的残缺。

博子在发现藤井树(女)时,她发现了他者,真实空间的“我”在那个地方映照出了虚拟空间的“我”,出现镜外我与镜中我的对视。
这种我与“我”的对视导致她的回忆出现裂痕,为亡夫编织的想象王国瞬间崩塌,后续的剧情也由此转变。
与此同时,在追求回忆的过程中,观者看到的一是夹杂着理想憧憬的主观感受,二是通过碎片化记忆拼凑出的假想形象。博子不能正确的定位自己,也不能区分自己和另一朵双生花,因此在实在界的主体性是还不存在的。

在藤井树(女)身上,死亡作为与藤井树(男)回忆中的叙事主干,藤井树(女)父亲的形象在电影中不断以片段浮现,都是围绕着他死于肺炎的场景。
父亲之名的缺席——真实父亲与父亲身份的缺失和死亡相联系。此时的“父亲”是不在场的,并无限缺席于家庭和自我人生中。
此处场景体现的缺失暗示着,藤井树(女)所处的生活与岁月同样存在缺口,她并非是一个幸福完满之人。在电影开始前,父亲缺席作为死亡的

阴影缠绕着她,她看似宁静的生活也有缺口存在。
父亲离世导致她无限逃避现实,藤井树(女)从而产生家庭破碎的印象。再者是藤井树(女)告别初恋时的羞涩失语,面对镜中他者藤井树的突然缺失,所展现的是掩盖藤井树(男)缺席后的失落与逃避。
其中,影片出现了“反复的感冒情节”,藤井树(女)借由感冒拒绝邮差的告白,在早餐桌旁对母亲的回答和忽略爷爷的反复要求等,表现了主体面临现实的缺席。
藤井树(女)无法从断裂的现实中搭建主体,虽然表现为遗忘,但却是实在域内一种精神上被迫的记忆屏蔽,而非象征介入后主体意识下的遗忘,此时的藤井树(女)在实在领域也不存在真正的主体。

创伤体验与主体错位
创伤具有一种精神性,是在外部的刺激下,由于主体无法理解并掌握这种冲突从而引发。在创伤的影响下,人类个体在真实与想象中感受到了其无法理解的东西,而这段无法同化的记忆将会被压抑和遗忘,以等待日后在某个时间通过些许无关紧要的事件重新将其带回现实意识。
同时,创伤是“实在的”,它无形的充斥在实在领域中,因为它是始终无法象征化的,并且是处在主体中心的一种永久的错位。创伤阻碍着象征化的运动,并使主体被迫固着在一个焦躁的发展阶段上。

记忆被主体铭记,并使其感知强烈的心理紊乱与精神痛苦,且无论他试图怎样去合理化并表达这段记忆,它都会不断地返回并重复着痛苦。
在《情书》中,我们同样可以寻找到这种遭受创伤的“病人”。藤井树(女)在少女时期,由于父亲的突然去世,以及感冒致死的打击,而深陷感冒的困扰中,并且对医院和药物带有着深深地恐惧之感。
然而单纯的心理恐惧并不足以构成创伤的全部,现实中藤井树(女)每每遇到生活的重大转折,都会不自觉的引发一场感冒,出现生理上的发烧、晕眩、幻觉的症状,甚者直面死亡。

藤井树(女)深深的陷入这种疾病折磨中,创伤使她将语言统治下的现实同想象分离。也正是这个创伤,能够使藤井树(女)在现实中更为清晰具象的感知到无形实在域的存在。
现实的死亡和离席是在现实中让主体崩溃的客体,而这份客体上加之象征指代,便成为了主体所经历中称之为疾病的存在。
具体来说,藤井树(女)第一次的创伤是重感冒后在医院产生的幻想,这揭开了藤井树(女)久久感冒复发的原因。
当她在幻想的回忆中目睹父亲在担架上空洞的眼神,与母亲和爷爷焦急的催赶后,镜头突然闪现出与藤井树(男)最后一次相见时的镜像。

这也说明了藤井树(女)的创伤在于目睹父亲的离世,同时也叠加了的少年树的离席。此时,快速闪过的泛白的镜头象征着幻想的虚幻,左右摇晃的镜头也在显示着主体在现实世界崩塌后的错位与不安。
藤井树(女)在直面死亡中迎来与实在域的交错相遇,自此她便无时无限的被实在包裹着,持续的陷入感冒困扰中。在拉康看来,实在域中的创伤感知将是主体中心的一种永恒错位。
主体在醒来之时,面对实在表象的归返,重新面对现实,同时又在不断地自我说服,编织自己的意识。此时的主体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错位并分裂。

实在表象的归返,是一种无意识的实在域的返回,当藤井树(女)回到现实,身上的感冒症状无法消退;从另一角度来看,她拥有的意识又可以知晓自己刚产生的幻觉,但她只能通过想象来遮掩自身的分裂症状,这便是来自实在域的凝视。
在凝视中,主体窥觊了自身欲望与主体欲望间的空洞,主体形成于其中并深陷其中,凝视一步步刺激着主体的错位更改。
【相关文章】
本文地址:https://www.qubaike.com/ent/0dvfkrux.html
声明:本文信息为网友自行发布旨在分享与大家阅读学习,文中的观点和立场与本站无关,如对文中内容有异议请联系处理。